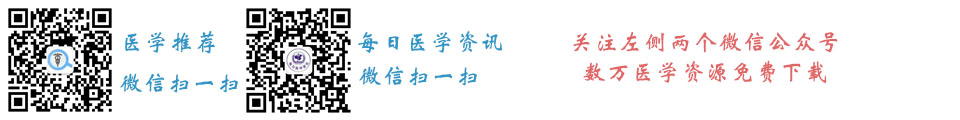读医学网
世卫换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局
发布时间:2017-06-03 09:38 类别:医学前沿资讯 标签:公共卫生 变局 来源:未知
2017 年 5 月 23 日,埃塞俄比亚人泰德罗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以超过 2 / 3 多数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第 70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当选为新一届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Director-General),并将于 7 月 1 日起开始其五年任期,接替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博士。
2017 年 5 月 23 日,埃塞俄比亚人泰德罗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以超过 2 / 3 多数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第 70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当选为新一届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Director-General),并将于 7 月 1 日起开始其五年任期,接替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博士。 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稿称,泰德罗斯博士曾先后担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2005-2012)和外交部长(2012-2016)。他还曾担任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全球基金,Global Fund)理事会主席;遏制疟疾伙伴关系(Roll-back Malaria)理事会主席,以及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卫生伙伴关系理事会联合主席。事实上,这位社区健康博士还位列埃塞俄比亚执政党 革命民主阵线 中央委员会委员。 应当说,泰德罗斯的当选,创造了一系列的纪录。他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 70 年以来,第一位非内科医生(Non-Physician)出身的和第一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也是第三位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总干事。更为重要的是,以往的总干事,均是通过有着 34 个成员的世卫执行委员会通过闭门的、精英化的秘密投票选出的。而泰德罗斯则是由 186 个成员单位(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三轮公开书面投票及匿名计票后,从三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 泰德罗斯的参选,得到了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大力支持。奥巴马政府盛赞其任卫生部长期间取得的成就:他领导了埃塞俄比亚卫生系统的全面改革工作,并重新塑造了该国卫生系统的愿景。他扩展了该国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了 3500 个医疗中心和 1.6 万个医疗点;在乡村层面培训了近 4 万名基层卫生工作者;他启动融资机制,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作为外交部长,他还领导了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的谈判工作,有 193 个国家承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必要资金。他在任全球基金理事会主席期间,推动反对欺诈和腐败等一系列改革,也得到奥巴马政府的欢心,因此美国令人惊讶地没有以埃塞俄比亚严重的人权问题作为反制 埃塞俄比亚在 Ogaden 地区和少数族裔问题上有着 可怕 的人权纪录,该国并且一味打压记者,近年来还试图通过立法将在该国提供法律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非法化。奥巴马政权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支持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原因,那就是一直以来其将埃塞当成该地区抗击 ISIS、伊斯兰青年运动(al-Shabab)和其他恐怖组织的支柱性国家。但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一关系的前景变得复杂化了。 泰德罗斯起初并不在共和党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法眼之内,特朗普所青睐的,是来自传统盟友英国的候选人、得到英国卫生大臣和国际发展大臣双重背书的戴维 纳巴罗(David Nabarro)。牛津出身的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纳巴罗有着全球国际组织任职的完整履历,他曾任世卫总干事办公室主任,并曾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一系列的联合国机构中担任过高管 因此,世卫大会此次的选择,可谓是一次不折不扣罕见的 逆鳞 之举。一些分析人士暗示,这可能置全球公共卫生于政策不确定的风险之中:特朗普政府新任命的卫生和人类服务署署长(即美国的卫生部长)、来自佐治亚州的前国会众议员汤姆 普莱斯(Tom Price)旋即于日内瓦世卫大会前,访问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毒的起源地之一)并 审视 2014 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各项设施状况。值得注意的是,纳巴罗 2014-2015 年间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埃博拉问题特使,并曾于 2005-2014 年间担任联合国系统禽流感和人类流感高级协调员(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级)。 汤姆 普莱斯对埃博拉故地的访问,可谓 哪壶不开提哪壶 。 1976 年,埃博拉病毒在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发现,并曾多次小范围爆发。2013 年,埃博拉在几内亚临近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边界 Gueckedou 州的一个村子里再次爆发,《新英格兰杂志》的研究显示病毒产生可追溯到该村一个死于埃博拉的两岁男孩,他的母亲、祖母和姐姐们随后也感染死亡,但病毒来源未可知。病毒随后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肆虐,并出现在了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马里。2015 年底,全球共计 28,600 人感染,11,300 死亡,2016 年 1 月,西非宣布解除疫情。在这一被称为是 当代最为严重和惨痛的卫生紧急状况 中,世界卫生组织因其内部松散的管理和对疫情迟滞的反应,遭到全球范围内严厉的抨击:全球非政府组织 无国界医生 于 2014 年 3 月就派遣救援人员赴西非,并于 3 月 31 日宣布疫情 前所未见 ,相比之下,老迈的世卫组织彼时则正陷于资金削减的苦恼,拖拖拉拉,直到该年 8 月才宣布公共卫生的全球紧急状态,而那时疫情在英美法诸国的联手狙击下,已经初步有所遏制。 为狙击埃博拉病毒,美国政府投入了 20 亿美金,并派驻军队和建立医疗后勤设施。世界银行则动员了 16 亿美金援助,盖茨基金会和 脸书 创始人扎克伯格夫妇则分别投入 5000 万和 2500 万美元捐助。但这些援助在疫情消退后,却被报道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2015 年 4 月《纽约时报》称,美国在利比里亚资助的 11 个治疗中心在 2014 年 11 月到 2015 年 1 月间,只接待了 28 个埃博拉患者。这引发了如何更好地动员本土资源抗击疾病、以及如何将国际援助更好地花在受援国卫生系统建设上的辩论。 这一系列质疑,以及过去十余年来以来围绕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展开的核心辩论 如何让发达国家承担全球公共卫生中的援助义务而又解决受援国本土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问题,以有效降低受援国的依赖性 为汤姆 普莱斯此行做了注脚。在利比亚和日内瓦世的几个场合的发言中,汤姆 普莱斯强调了公共卫生安全(Global Health Security)的重要性,这包括了疫情和疾病的爆发,以及生化恐怖主义(Bio-terrorism)问题。他敦促世界卫生组织需要 集中精力于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之应对 ,称必须将这一工作作为世卫的 头号优先工作选项 (must be its number one priority)。他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称: 我们期待下一任总干事将这些威胁作为优先选项,包括传染性疾病问题。 在日内瓦的另一个场合发言时,他强调称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绝对是美国的优先考量 。 这显然是在和新当选的总干事泰德罗斯唱对台戏,泰德罗斯一贯声称 推进全民健保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是他的工作重点,也是全球卫生工作重中之重,而对紧急疫情(包括流行病和传染性疾病)的反应能力建设,乃是总干事次一等的要务。泰德罗斯试图努力满足来自非洲大陆的高度期待 提升对非洲的公共卫生援助和解决非洲严峻的健保挑战 正如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指出的,这是一个 非洲的时刻 , 未来属于非洲 。然而,泰德罗斯这一充满 大庇天下寒士 的豪情,虽然和奥巴马在任时力推的国内健保法案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时过境迁,他现在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右翼卷土重来的西方世界,尤其是右翼主导下的美国参众两院和一个处处声称 美国优先 的商人总统。2017 年 5 月 4 日,联邦众议院以 217:213 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修改版的新健保法案,迈出了废除了奥巴马健保法案的重大一步。 泰德罗斯的困局是显而易见的,而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字:钱。 就在世界卫生大会如火如荼举办期间,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美国 2018 财年预算,该预算大幅削减了对全球公共卫生项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一系列对外援助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资助。雪上加霜的是,在随后举办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向北约各成员国 逼债 ,要求他们每年履行缴纳自身 GDP2% 的 保护费 ,这无疑进一步挤压了本来就处于权力角逐弱势地位的全球公共卫生的资源索取空间,压缩了其全球蛋糕基本盘。该预算将美国对外援助预算降低了 1 /3,砍掉了 不能充分证明自身正面效应 的项目以及未得到国会立法授权的项目(包括 11 亿美金的购置艾滋病抗病毒药物费用,以及对疟疾和脊髓灰质炎项目的资助等)。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是世卫和其他相关国际公卫机构的主要资助方,2016 年美国政府对世卫的资助是 3.05 亿美金,盖茨基金会则为 1.82 亿美金。而今年盖茨基金会则已经超过了美国政府,成为世卫最大的资金来源,但基金会方面因担心世卫的过度依赖,已经明确表态不会补足美国政府减少的资助部分,并为资助设定了最高限额。 本次世卫大会批准的 44 亿美金的预算中,约 8 亿投向传染性疾病,3.5 亿投向慢病,5.9 亿投向地方卫生系统建设,5.54 亿投向公共卫生应急(去年是 4.3 亿)。但这一预算只是纸面上的,总干事需要去筹资后才能花销,而 80% 的世卫资金来自于筹资而非会费等强制缴费,因此世卫资金运作屡屡亮出红灯,并在过去数年中进行了大规模裁员。 更糟糕的是,世卫还因为其工作的成功而付出代价:全球正处于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临界点(如果消灭,其将成为自天花后第二个被人类消灭的传染病),目前只存在于尼日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且今年全球只查出 5 例。但是这却让世卫的 全球脊髓灰质炎行动 项目陷入困局,这个项目过去是世卫的一只 会下金蛋的鸡 ,但现在则面临被砍的命运。世卫的资料显示,该项目的资金过去被用于世卫的工资支付、资助有困难的国家(如刚果),其资金占世卫工资比为 1 /7,74% 的世卫非洲区雇员的工资来源于该项目资金;数十年来,该项目资金还被用来支付安哥拉、乍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甚至一些早已没有脊髓灰质炎国家的一半卫生系统官员的工资。自 1988 年以来,该项目资金已经成为世卫的 压舱石 (2008 年以前,世卫曾经可以染指全球基金这一巨额资金池,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世卫和全球基金进行了人事剥离,全球基金成了完全独立的机构,世卫的资金池被压缩了),正如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 Laurie Garrett 总结指出的,如果该项目 消失 ,那么对世卫来说,就可谓前途叵测了。 显然,雄心万丈的泰德罗斯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接下来的两年内,他无法完成融资任务,他会 目睹纸牌屋的坍塌 。作为职场老手,老资格的政客泰德罗斯明白,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中的拖沓和糟糕表现,让世卫背负了巨大的 政治负资产 。他做出承诺,要把世卫改造成一个 可信和诚实 的组织,并提升应对问题的能力和资金管理的透明度(但就在他做出这些承诺的当口,美联社爆料世卫仅在埃博拉期间的差旅费用就超过 2.3 美金,远超其 2016 年在艾滋病、结核、疟疾和肝炎等传染性疾病治疗上的投资)。他也坦陈,世卫需要将资金移向 优先 选项,当然,这些 优先选项 是否会和他一贯声称的 推进全球健保 计划 暗合 ,就不得而知了。 随着美国政府对外援助预算额大幅削减和盖茨基金会等援助机构的低调因应,泰德罗斯必须将目光投向其他的潜在资助方,比如 G20 国家以及其他的私营部门。但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这几年普遍陷入困境,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许多 G20 国家,也面临着巨大的公共卫生挑战。印度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数位于全球前列,炎热的气候和不良的卫生习惯,更让其卫生系统雪上加霜。近十年来,由于 GDP 高速发展,印度空气和环境污染加剧,慢病挑战的阴影已经悄然浮现。而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目前更有着 3 亿人受到慢病困扰,这一数字超过非洲人口总数的 1 /3。我们很难想象(即便是对那些最热心于援助非洲的公益人士而言),拿一国纳税人的资金去资助其他国家和地区健保,会在本国民众中引发广泛而由衷的赞善之情 这恰是为什么德国不愿意救助希腊债务危机的基本原因。 进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将自身的发展,完全寄希望于外部援助。2009 年,Dambisa MOYO 在华尔街日报的那篇名为 Why Foreign Aid is Hurting Africa (《为什么对外援助正在伤害着非洲》)的雄文中,痛陈利害:在过去 60 年中,富国以对外援助名义给了非洲超过 1 万亿美金的援助,但其人均收入却低于 20 世纪 70 年代。每天的生活费低于 1 美金的人口达到 3.5 亿,超过该大陆总人口的一半,20 年来翻了一番。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现实,它告诉人们,如果不能完善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水平,仅靠外部援助 扶贫 ,不仅不能起到效果,恰恰相反,在一些区域,这些白得的、缺乏监管的钱(free money),还会给该国或地区,加上一个 腐败 的车轮,让其彻底走向治理失灵。前文中为泰德罗斯当选鼓与呼的非盟,在 2002 年时也曾指出,腐败让非洲大陆每年损失 1500 亿美金,而国际捐助方们却往往视而不见。 不惟如是,这些白得的钱,还滋长了受援地区政府官员、某些国际政府间组织等试图靠外援项目获益的冲动。以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的全球基金为例,由于非洲各国早先普遍缺少合格的政府管理或本土非政府组织,因此 UNDP(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在许多非洲国家扮演了全球基金资助资金的 PR(一级资金接收方)角色,但研究却表明,UNDP 在诸多 PR 中效率最为低下。 在全球卫生领域,围绕着国际援助资金,还产生了一个国际-国内非政府组织 掮客 的巨大利益链。由于监管的普遍缺失,这一利益链的资金耗损和投入产出效益,目前无法评估。但有趣的是,不止一个国家不仅不去立法让这些机构的管理更加透明,反倒采取 一刀切 措施,试图将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 非法化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因治理环境得不到提升而鱼龙混杂;另一方面,以外交优先主义的名义排斥(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在增强了政府(以及和政府较为接近的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资源把控力的同时,却削弱了民间社会对官僚机构滥用权力的天然制衡作用。所以,一手纵容,一手打压,不过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罢了。随着全球范围内对治理和透明度的呼声渐长,对外援助模式出现变更的迹象,过去接受援助的政府和国际组织首先感受到了寒意,但讽刺的是,由于非政府组织一直以来是对外援助的一条重要通道,在这一通道因 非法化 问题受阻后,这些政府和国际组织发现,他们陷入了 作茧自缚 的境地。 作为前全球基金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主席,泰德罗斯博士有着良好的筹资能力,他曾经使两个组织筹集到了创纪录的资金,并制定了《全球疟疾行动计划》,这使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扩大到了非洲以外的亚洲和拉丁美洲。但是,筹资是一回事,治理的理念、尤其是面对全新的全球公卫挑战而亟需的创造性和回应性并举的理念,则是另一回事。在一个经济紧缩和全球化遇阻的时代,对(国际组织)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的要求,响彻全球。这与其说是因为 廉洁 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毋宁说是因为可供挥霍的资源变得更加稀缺而资金争夺战则愈演愈烈,而各利害相关方的利益则亟需平衡。全球不确定性的前景,以及区域冲突、贫困、治理失灵、灾难和饥荒及环境变迁,使得人类面临空前的公共卫生(疾病流行、病毒变异加速、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及次生灾害的挑战)。因此,如何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透明度和责任制(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已经成为下一步变革的题中之义。全球公卫治理不应当是政府或国际政府间组织的 独角戏 ,而应该是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受疾病困扰人群及其他各利害相关方共同努力的网络和平台,只有提升全球公共参与和透明度,才能让全球受疾病影响人群的声音为人所知,才能最大限度地让资源合理流向最需要得到帮助、支持的群体,也才能够为争取全球公共卫生资源的合理份额,进行强有力的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讲,世卫在未来筹资的结果,固然涉及其生死存亡,但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而言,更重要的,却是迎接变革与新生,并以全新的面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的不确定性挑战。
2017 年 5 月 23 日,埃塞俄比亚人泰德罗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以超过 2 / 3 多数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第 70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当选为新一届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Director-General),并将于 7 月 1 日起开始其五年任期,接替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博士。 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稿称,泰德罗斯博士曾先后担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2005-2012)和外交部长(2012-2016)。他还曾担任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全球基金,Global Fund)理事会主席;遏制疟疾伙伴关系(Roll-back Malaria)理事会主席,以及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卫生伙伴关系理事会联合主席。事实上,这位社区健康博士还位列埃塞俄比亚执政党 革命民主阵线 中央委员会委员。 应当说,泰德罗斯的当选,创造了一系列的纪录。他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 70 年以来,第一位非内科医生(Non-Physician)出身的和第一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也是第三位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总干事。更为重要的是,以往的总干事,均是通过有着 34 个成员的世卫执行委员会通过闭门的、精英化的秘密投票选出的。而泰德罗斯则是由 186 个成员单位(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三轮公开书面投票及匿名计票后,从三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 泰德罗斯的参选,得到了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大力支持。奥巴马政府盛赞其任卫生部长期间取得的成就:他领导了埃塞俄比亚卫生系统的全面改革工作,并重新塑造了该国卫生系统的愿景。他扩展了该国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了 3500 个医疗中心和 1.6 万个医疗点;在乡村层面培训了近 4 万名基层卫生工作者;他启动融资机制,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作为外交部长,他还领导了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的谈判工作,有 193 个国家承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必要资金。他在任全球基金理事会主席期间,推动反对欺诈和腐败等一系列改革,也得到奥巴马政府的欢心,因此美国令人惊讶地没有以埃塞俄比亚严重的人权问题作为反制 埃塞俄比亚在 Ogaden 地区和少数族裔问题上有着 可怕 的人权纪录,该国并且一味打压记者,近年来还试图通过立法将在该国提供法律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非法化。奥巴马政权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支持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原因,那就是一直以来其将埃塞当成该地区抗击 ISIS、伊斯兰青年运动(al-Shabab)和其他恐怖组织的支柱性国家。但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一关系的前景变得复杂化了。 泰德罗斯起初并不在共和党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法眼之内,特朗普所青睐的,是来自传统盟友英国的候选人、得到英国卫生大臣和国际发展大臣双重背书的戴维 纳巴罗(David Nabarro)。牛津出身的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纳巴罗有着全球国际组织任职的完整履历,他曾任世卫总干事办公室主任,并曾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一系列的联合国机构中担任过高管 因此,世卫大会此次的选择,可谓是一次不折不扣罕见的 逆鳞 之举。一些分析人士暗示,这可能置全球公共卫生于政策不确定的风险之中:特朗普政府新任命的卫生和人类服务署署长(即美国的卫生部长)、来自佐治亚州的前国会众议员汤姆 普莱斯(Tom Price)旋即于日内瓦世卫大会前,访问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毒的起源地之一)并 审视 2014 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各项设施状况。值得注意的是,纳巴罗 2014-2015 年间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埃博拉问题特使,并曾于 2005-2014 年间担任联合国系统禽流感和人类流感高级协调员(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级)。 汤姆 普莱斯对埃博拉故地的访问,可谓 哪壶不开提哪壶 。 1976 年,埃博拉病毒在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发现,并曾多次小范围爆发。2013 年,埃博拉在几内亚临近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边界 Gueckedou 州的一个村子里再次爆发,《新英格兰杂志》的研究显示病毒产生可追溯到该村一个死于埃博拉的两岁男孩,他的母亲、祖母和姐姐们随后也感染死亡,但病毒来源未可知。病毒随后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肆虐,并出现在了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马里。2015 年底,全球共计 28,600 人感染,11,300 死亡,2016 年 1 月,西非宣布解除疫情。在这一被称为是 当代最为严重和惨痛的卫生紧急状况 中,世界卫生组织因其内部松散的管理和对疫情迟滞的反应,遭到全球范围内严厉的抨击:全球非政府组织 无国界医生 于 2014 年 3 月就派遣救援人员赴西非,并于 3 月 31 日宣布疫情 前所未见 ,相比之下,老迈的世卫组织彼时则正陷于资金削减的苦恼,拖拖拉拉,直到该年 8 月才宣布公共卫生的全球紧急状态,而那时疫情在英美法诸国的联手狙击下,已经初步有所遏制。 为狙击埃博拉病毒,美国政府投入了 20 亿美金,并派驻军队和建立医疗后勤设施。世界银行则动员了 16 亿美金援助,盖茨基金会和 脸书 创始人扎克伯格夫妇则分别投入 5000 万和 2500 万美元捐助。但这些援助在疫情消退后,却被报道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2015 年 4 月《纽约时报》称,美国在利比里亚资助的 11 个治疗中心在 2014 年 11 月到 2015 年 1 月间,只接待了 28 个埃博拉患者。这引发了如何更好地动员本土资源抗击疾病、以及如何将国际援助更好地花在受援国卫生系统建设上的辩论。 这一系列质疑,以及过去十余年来以来围绕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展开的核心辩论 如何让发达国家承担全球公共卫生中的援助义务而又解决受援国本土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问题,以有效降低受援国的依赖性 为汤姆 普莱斯此行做了注脚。在利比亚和日内瓦世的几个场合的发言中,汤姆 普莱斯强调了公共卫生安全(Global Health Security)的重要性,这包括了疫情和疾病的爆发,以及生化恐怖主义(Bio-terrorism)问题。他敦促世界卫生组织需要 集中精力于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之应对 ,称必须将这一工作作为世卫的 头号优先工作选项 (must be its number one priority)。他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称: 我们期待下一任总干事将这些威胁作为优先选项,包括传染性疾病问题。 在日内瓦的另一个场合发言时,他强调称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绝对是美国的优先考量 。 这显然是在和新当选的总干事泰德罗斯唱对台戏,泰德罗斯一贯声称 推进全民健保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是他的工作重点,也是全球卫生工作重中之重,而对紧急疫情(包括流行病和传染性疾病)的反应能力建设,乃是总干事次一等的要务。泰德罗斯试图努力满足来自非洲大陆的高度期待 提升对非洲的公共卫生援助和解决非洲严峻的健保挑战 正如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指出的,这是一个 非洲的时刻 , 未来属于非洲 。然而,泰德罗斯这一充满 大庇天下寒士 的豪情,虽然和奥巴马在任时力推的国内健保法案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时过境迁,他现在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右翼卷土重来的西方世界,尤其是右翼主导下的美国参众两院和一个处处声称 美国优先 的商人总统。2017 年 5 月 4 日,联邦众议院以 217:213 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修改版的新健保法案,迈出了废除了奥巴马健保法案的重大一步。 泰德罗斯的困局是显而易见的,而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字:钱。 就在世界卫生大会如火如荼举办期间,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美国 2018 财年预算,该预算大幅削减了对全球公共卫生项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一系列对外援助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资助。雪上加霜的是,在随后举办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向北约各成员国 逼债 ,要求他们每年履行缴纳自身 GDP2% 的 保护费 ,这无疑进一步挤压了本来就处于权力角逐弱势地位的全球公共卫生的资源索取空间,压缩了其全球蛋糕基本盘。该预算将美国对外援助预算降低了 1 /3,砍掉了 不能充分证明自身正面效应 的项目以及未得到国会立法授权的项目(包括 11 亿美金的购置艾滋病抗病毒药物费用,以及对疟疾和脊髓灰质炎项目的资助等)。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是世卫和其他相关国际公卫机构的主要资助方,2016 年美国政府对世卫的资助是 3.05 亿美金,盖茨基金会则为 1.82 亿美金。而今年盖茨基金会则已经超过了美国政府,成为世卫最大的资金来源,但基金会方面因担心世卫的过度依赖,已经明确表态不会补足美国政府减少的资助部分,并为资助设定了最高限额。 本次世卫大会批准的 44 亿美金的预算中,约 8 亿投向传染性疾病,3.5 亿投向慢病,5.9 亿投向地方卫生系统建设,5.54 亿投向公共卫生应急(去年是 4.3 亿)。但这一预算只是纸面上的,总干事需要去筹资后才能花销,而 80% 的世卫资金来自于筹资而非会费等强制缴费,因此世卫资金运作屡屡亮出红灯,并在过去数年中进行了大规模裁员。 更糟糕的是,世卫还因为其工作的成功而付出代价:全球正处于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临界点(如果消灭,其将成为自天花后第二个被人类消灭的传染病),目前只存在于尼日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且今年全球只查出 5 例。但是这却让世卫的 全球脊髓灰质炎行动 项目陷入困局,这个项目过去是世卫的一只 会下金蛋的鸡 ,但现在则面临被砍的命运。世卫的资料显示,该项目的资金过去被用于世卫的工资支付、资助有困难的国家(如刚果),其资金占世卫工资比为 1 /7,74% 的世卫非洲区雇员的工资来源于该项目资金;数十年来,该项目资金还被用来支付安哥拉、乍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甚至一些早已没有脊髓灰质炎国家的一半卫生系统官员的工资。自 1988 年以来,该项目资金已经成为世卫的 压舱石 (2008 年以前,世卫曾经可以染指全球基金这一巨额资金池,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世卫和全球基金进行了人事剥离,全球基金成了完全独立的机构,世卫的资金池被压缩了),正如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 Laurie Garrett 总结指出的,如果该项目 消失 ,那么对世卫来说,就可谓前途叵测了。 显然,雄心万丈的泰德罗斯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接下来的两年内,他无法完成融资任务,他会 目睹纸牌屋的坍塌 。作为职场老手,老资格的政客泰德罗斯明白,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中的拖沓和糟糕表现,让世卫背负了巨大的 政治负资产 。他做出承诺,要把世卫改造成一个 可信和诚实 的组织,并提升应对问题的能力和资金管理的透明度(但就在他做出这些承诺的当口,美联社爆料世卫仅在埃博拉期间的差旅费用就超过 2.3 美金,远超其 2016 年在艾滋病、结核、疟疾和肝炎等传染性疾病治疗上的投资)。他也坦陈,世卫需要将资金移向 优先 选项,当然,这些 优先选项 是否会和他一贯声称的 推进全球健保 计划 暗合 ,就不得而知了。 随着美国政府对外援助预算额大幅削减和盖茨基金会等援助机构的低调因应,泰德罗斯必须将目光投向其他的潜在资助方,比如 G20 国家以及其他的私营部门。但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这几年普遍陷入困境,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许多 G20 国家,也面临着巨大的公共卫生挑战。印度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数位于全球前列,炎热的气候和不良的卫生习惯,更让其卫生系统雪上加霜。近十年来,由于 GDP 高速发展,印度空气和环境污染加剧,慢病挑战的阴影已经悄然浮现。而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目前更有着 3 亿人受到慢病困扰,这一数字超过非洲人口总数的 1 /3。我们很难想象(即便是对那些最热心于援助非洲的公益人士而言),拿一国纳税人的资金去资助其他国家和地区健保,会在本国民众中引发广泛而由衷的赞善之情 这恰是为什么德国不愿意救助希腊债务危机的基本原因。 进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将自身的发展,完全寄希望于外部援助。2009 年,Dambisa MOYO 在华尔街日报的那篇名为 Why Foreign Aid is Hurting Africa (《为什么对外援助正在伤害着非洲》)的雄文中,痛陈利害:在过去 60 年中,富国以对外援助名义给了非洲超过 1 万亿美金的援助,但其人均收入却低于 20 世纪 70 年代。每天的生活费低于 1 美金的人口达到 3.5 亿,超过该大陆总人口的一半,20 年来翻了一番。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现实,它告诉人们,如果不能完善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水平,仅靠外部援助 扶贫 ,不仅不能起到效果,恰恰相反,在一些区域,这些白得的、缺乏监管的钱(free money),还会给该国或地区,加上一个 腐败 的车轮,让其彻底走向治理失灵。前文中为泰德罗斯当选鼓与呼的非盟,在 2002 年时也曾指出,腐败让非洲大陆每年损失 1500 亿美金,而国际捐助方们却往往视而不见。 不惟如是,这些白得的钱,还滋长了受援地区政府官员、某些国际政府间组织等试图靠外援项目获益的冲动。以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的全球基金为例,由于非洲各国早先普遍缺少合格的政府管理或本土非政府组织,因此 UNDP(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在许多非洲国家扮演了全球基金资助资金的 PR(一级资金接收方)角色,但研究却表明,UNDP 在诸多 PR 中效率最为低下。 在全球卫生领域,围绕着国际援助资金,还产生了一个国际-国内非政府组织 掮客 的巨大利益链。由于监管的普遍缺失,这一利益链的资金耗损和投入产出效益,目前无法评估。但有趣的是,不止一个国家不仅不去立法让这些机构的管理更加透明,反倒采取 一刀切 措施,试图将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 非法化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因治理环境得不到提升而鱼龙混杂;另一方面,以外交优先主义的名义排斥(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在增强了政府(以及和政府较为接近的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资源把控力的同时,却削弱了民间社会对官僚机构滥用权力的天然制衡作用。所以,一手纵容,一手打压,不过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罢了。随着全球范围内对治理和透明度的呼声渐长,对外援助模式出现变更的迹象,过去接受援助的政府和国际组织首先感受到了寒意,但讽刺的是,由于非政府组织一直以来是对外援助的一条重要通道,在这一通道因 非法化 问题受阻后,这些政府和国际组织发现,他们陷入了 作茧自缚 的境地。 作为前全球基金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主席,泰德罗斯博士有着良好的筹资能力,他曾经使两个组织筹集到了创纪录的资金,并制定了《全球疟疾行动计划》,这使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扩大到了非洲以外的亚洲和拉丁美洲。但是,筹资是一回事,治理的理念、尤其是面对全新的全球公卫挑战而亟需的创造性和回应性并举的理念,则是另一回事。在一个经济紧缩和全球化遇阻的时代,对(国际组织)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的要求,响彻全球。这与其说是因为 廉洁 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毋宁说是因为可供挥霍的资源变得更加稀缺而资金争夺战则愈演愈烈,而各利害相关方的利益则亟需平衡。全球不确定性的前景,以及区域冲突、贫困、治理失灵、灾难和饥荒及环境变迁,使得人类面临空前的公共卫生(疾病流行、病毒变异加速、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及次生灾害的挑战)。因此,如何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透明度和责任制(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已经成为下一步变革的题中之义。全球公卫治理不应当是政府或国际政府间组织的 独角戏 ,而应该是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受疾病困扰人群及其他各利害相关方共同努力的网络和平台,只有提升全球公共参与和透明度,才能让全球受疾病影响人群的声音为人所知,才能最大限度地让资源合理流向最需要得到帮助、支持的群体,也才能够为争取全球公共卫生资源的合理份额,进行强有力的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讲,世卫在未来筹资的结果,固然涉及其生死存亡,但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而言,更重要的,却是迎接变革与新生,并以全新的面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的不确定性挑战。
- 猜你会喜欢....